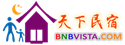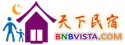1998年独自去西藏,在拉萨邂逅一对重庆夫妇,与他们搭伴从拉萨到日喀则到江孜经浪卡子走羊卓雍错回到拉萨。那时从拉萨到日喀则的新路刚修好,从江孜经浪卡子和羊卓雍错到拉萨的老路很烂。此文写于1999年,并同年刊于《旅游》第5期。
那天清晨,江孜城仍在沉睡之中,雾还厚厚地缭绕在白居寺的十万佛塔上,我已经开始在大街上转,希望找到一辆经羊卓雍湖回到拉萨的车。打听了许多车,司机们宁愿费事费时走由江孜到日喀则、再由日喀则回到拉萨的新路,也不愿意走这条回拉萨的老路。因为连日阴雨发大水,老路已经断掉多处,而且翻浆泥泞得厉害,走起来十分困难。他们指指一些大腿上还留着泥浆痕迹的游客说,这些人是趟着快齐腰深的洪水用了两天的时间由羊卓雍措过来的,没有司机愿意冒这个风险。

1998年水大,去日喀则路上的一座桥被冲垮。照片扫描
道路的情况我知道,但我想已经有一天一夜没下雨了,加上有人修路,路况一定会好转,我一定能看到西藏第二大神湖羊卓雍措。抱着这个信念,我执著地在江孜的街上游走询问每一辆等活儿的司机,偶尔碰上愿意走的,一定要走两天,而且要价之高,使我顿生走了这一趟就没钱回北京的恐惧。

1998年由江孜到羊湖的路。照片扫描

2006年羊湖边上的很好的柏油路,数码照片。
太阳升起来了,灿烂的阳光照在了江孜抗英英雄城堡的顶上,无家的狗开始在刚支起的肉摊旁边等待布施,街上嘈杂了起来。我和同伴的心情十分焦急,因为再拖下去,就无法在当天回到拉萨。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,稀薄的天空无情地消耗着体力,我们在不大的街上费劲地转着圈,同车主讨价的声音越来越低,喘息声越来越大,越来越粗。就在几近绝望的时候,从街的拐角处歪歪斜斜地开来一辆破北京吉普,停在了等活儿的车队中。
这辆破吉普,在那些沙漠王、切诺基、依维柯中活像一个穷困潦倒的小老头,从车上下来的司机,更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小老头。他穿着一身蓝色的旧线衣,外套一件油渍麻花的西装,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国防绿军帽。绝望之极的我们过去询问,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。我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再问,回答十分明确:走老路回拉萨,一定让你们看到羊卓雍措,一定在当晚回到拉萨,而且是在21∶00左右。激动之余忙问价钱,回答是1000元一趟,可乘5人。按惯例我们开始砍价到800元,老头略一思索,也同意了。旁边看热闹的藏族司机听到这个价钱都不干了,用藏语责骂他,于是价格最终定在了900元。
我赶忙招来了两个路上认识的老外,将条件讲给他们听。这样我们可以分担费用,同时心中窃想,一旦路上车子有个三长两短,这两个人高马大的老外也是推车的壮劳力。谁知乍一听他们很高兴,可一看到那辆破旧的车呀,脸色便由晴转阴。他们将这破车里外打量,又猫腰看了轮胎和底盘,十分严肃地对我说,这车太破太危险了,我们实在不信任它,建议你们也不要租。看着他们郑重的样子,我便仔细地打量起车来。
这是怎样一辆破车:没有打火的装置,用两根电线一接,再踩油门,就算着车了;没有喇叭键,用一根电线在铁板上戳一戳,汽车就发出瓮声瓮气的鸣叫,没有右视灯和转向灯,两侧没有玻璃,前面没有雨刷,活活一个发动机上架个铁皮棚子再放上两排椅子就向前开行。我心中打鼓,就去看那司机。
司机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们围着车子转,安然地回答我的询问和怀疑。好象他有一种定力,不知怎的,我开始相信这个老头,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无法回到拉萨。和同伴一商量,我们三个人爬上了这辆破车。司机不好意思地将两盒烟交到我们手中,请我们一路上为他点烟。一阵乱抖,车子启动了,驶出江孜的时候,还没有一辆车出行。我看到那些找车的游客用惊讶、怜悯和担心的目光看着我们,等着拉活的年轻人们幸灾乐祸地吹着口哨,我想他们一定觉得我们疯了。